活在都市里的人,大多对生活感到不太满意。数起来理由一堆:雾霾;加班;吃不到有菜味儿的菜;找不到没房没车的爱情;很久没笑过,又不知为何;心里憋得慌,却无以诉说;想找个朋友静静呆会儿,打开手机通讯录划完几十页,又默默关上…
有人一直做着逃离的梦,幻想找到一处有花儿,有天空,有尊严和自由的地方。于是,云南大理,凭借其蔚蓝的海、干净的云、苍色的山,慢悠悠的生活,成了越来越多人心目中「别处」的代表地。
容宴蓝和老公perez,就是一对辞去工作,处理掉北京的房产,逃离到大理的夫妻。
来大理之前,容宴蓝在北京一家西班牙语培训机构工作,那是她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七年的地方。不知是否和爱情一样,七年一到便准时发痒:她对枯燥重复、经常加班的工作厌烦透了。做电脑工程师的老公perez也常常黑白颠倒地写代码。两人天天面对面,却像分居了很多年。爱情仿佛早就败光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婚姻都保不住。两人商量坐下来好好聊聊,生活究竟该怎样进行下去。

经过一番诚恳的彻夜长谈,容宴蓝和perez决定来一场拯救生活拯救爱情的旅行:从北京出发,自驾去大理。
半个月过去了,容宴蓝仿佛度过了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她和perez住进洱海边一家安静的客栈,在雨季的云雾中似醒非醒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一起在温柔的月亮下喝酒跳舞;一起相拥看落地窗外金黄的光,她在光里给他读自己喜欢的诗…他们喜欢这里的阳光、这里的云和雨。
「生活本该是这样。留下来吧,就在这里。」容宴蓝提议。
「我也这么想」。
可怎么留呢?
「开一家客栈!」
两人不谋而合。对于没什么工业和企业的大理来说,「开客栈」,成了想留下来安居的人最容易想到的方式。容宴蓝对perez描述心目中小院的模样:干净、浪漫、人与人之间简单、真诚。用她喜欢的一句话说「与有情人做快乐事,莫问是劫是缘」。
两人火速启程回京,张罗着卖掉了北京的房产。那是他们用最美的青春,不分白天黑夜,打拼了近十年获得的一切。可现在,他们一心只想在客栈的天台喝酒,屋里喂猫,窗台养花,迎接来来往往的有缘人,听他们的故事,在苍山下、洱海旁「温柔过活、慢慢老去」。
一卖完房子,两人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大理,说干就干:找地方,办许可证,设计装修,安全测评,寻找网上合作平台…从一睁眼,到晚上瘫坐在床上才发现,该做的事儿仿佛永远都做不完。四个月过去了,他们在洱海边的客栈好不容易正式开张,又发现不得不开始担心投入的钱能不能赚的回来的问题。
当老板的日子与想象中的大不相同:虽然雇了两个小工,但很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小工一周休一天,他们却一刻也不能放松:家具要搬、床单要洗、下水道堵了要清、客人有问题要立即处理、各种宣传和活动要策划…求人帮忙时遭受的白眼,夫妻两都受够了,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
七八月,大理的雨季同时也是旺季来临了。客栈里挤满了人。游客们经常碰到下雨出不去,便一堆堆待在客栈里。容宴蓝要忙客栈的杂事,perez只好来招呼客人,陪他们聊天,向他们解释一切,回答一批又一批客人相同的问题。时间久了,他开始烦得不行,通常在一顿尬聊后就跑去天台找流浪歌手阿青抽烟,吐槽之后骂一句:傻x!
不久,孩子出生后。两人好不容易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却又逃不过在夜里被婴儿的哭闹反复折磨。一次perez又逃到了天台,窝在躺椅上烟还没来得及抽完一支,容宴蓝就嚷嚷着让他下楼去照顾女儿,陪客人聊天。perez懒懒地不想动,妻子便冲上来大骂:
「我们要买菜做饭啊,要打扫卫生啊!昨天换下来的床单现在还堆院子里!」
perez抱着头,沮丧地蹲在地上「我只想好好洗半小时的澡,再安静地睡两小时觉…」
忙碌过恼人的旺季,转眼到了冬天。这时的客栈除了号称来大理寻找灵感的歌手阿青,还有来寻找爱情的秦紫两个常住客,基本没什么人。容宴蓝算了一下,整年赚的钱还不如在北京上班时多。perez大大咧咧,容宴蓝却因为急速缩水的积蓄和入不敷出的状况整夜睡不着觉。
一切都与当初设想的那么不同: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出去玩儿了。这个承载了他们美丽梦想的客栈,变成了一个让他们寸步难离的笼子。甚至连他们的私人空间也遭到了挤压——为了腾出大间的客房,他们搬到了楼梯下面一间窄窄的小屋里。累了就洗洗睡,明天又是相同的一天。
而纷至沓来的旅客们,也并不都是「有缘人」。相当一部分让他们感到污龊:猥琐的大叔在男女混住的房间里偷偷躺在女生床位上蠕动被发现,不爱干净的小青年撒尿在啤酒瓶里放在床底不清理,浑身是戏的大妈因为给她留的停车位不够宽敞骂得他们狗血淋头…
容宴蓝还赶走过一个三天两头带不同的男人回来在洗衣房里乱搞的中年女人;也曾经被同行找痞子来客栈找茬、敲竹杠;还被看起来本分老实的当地修理工欺骗,用劣质材料修理下水管,导致一间客房常年漏水…
一切,都像是在做梦。
傍晚时分,容宴蓝站在天台上,俯瞰华灯初上的古城大理。不远处,洋人街和人民路的酒吧开启了新一天的嘈杂。她心想:其实这座古城跟北京并没有什么不同。吃喝拉撒,饮食男女。
来这里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云淡风轻、自由自我、享受闲静,却都带着各自心中不变的魔怔。一个个心魔作伴、聚集于此,却期盼能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获得重生。而所谓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不过是一块块关于灯红酒绿、欲望与焦虑的庸常戏剧背后不变的幕布。
清晨六点,吃过经常光顾的那家卤肉饭,阿青喜欢买一瓶当地的大理啤酒,最便宜的那种只要两块五,穿过嘈杂的洋人街,到处逛逛,再走出古镇,回到租住的容宴蓝客栈的阁楼上。最近,他总会下意识地穿过那个巷子,巷子两边有一个个女人,用薄薄的裙子裹着丰腴的屁股,站在路边,冲路过的男人暧昧地笑。
果然,晚上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摇滚乐,讲农村来到城市一无所有的年轻工人要用锤子锤出一个新世界。客人们面面相觑、反应沉闷。老板忙走上前去,对又唱又跳、竭力嘶喊后意犹未尽的阿青说:
「今晚上客人多,咱唱点大家都喜欢的。」
阿青笑了笑,坐下来,唱起了一首怀念前任女友的歌。与其说是唱,更像是呢喃,自说自话间夹杂着平日生活的嬉笑怒骂。客人有的坐不住了,传来嘘声和哂笑。老板面带愠色,过去打断了阿青:
「我来唱一首,你帮我伴奏。」阿青只好让出座位,站在一旁拿起了吉他。
「一首『南山南』送给大家,祝大家都能在这美丽的南方,找到自己难忘的小伙儿,或者姑娘!」
老板油滑地笑着,唱了起来: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这他妈唱的什么狗屁!」
阿青看着唱功平庸的老板紧闭双眼、神情微醺、夸张地摇晃巨大的头颅,心中不忿,就把手中的吉他弹得越来越快。老板的歌被阿青的节奏从抒情带成了RAP,最后只得说:
「慢点,慢点!你这节奏我跟不了。」
「每次他一发骚,老子就用节奏把他压下去!」阿青后来得意地对perez说。
虽然遭老板排挤,也少有人赏识,但阿青坚持自己的音乐「好的东西都要有生命力。不管是悲是喜,不能是没来由的犯贱!没妞儿泡也不要紧:
「老子写歌不为了谁!」
但他也明白,艺术需要用作品说话,而现在自己写的歌总共也不到5首,心中没有底气。阿青感到心中郁结了许多东西,有时会在暗夜里折磨他,却不能表达。
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他从酒与女人身上寻找灵感。但灵感对于他来说究竟有多重要,能不能变成作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酒是常喝的。大理的啤酒和劣质青梅酒,喝多了也管醉,只是第二天头会很痛。喝醉了,就可以「飞起来」,感觉强烈的光线里包含奇妙而多变的音乐,自己在骑着沙发飞升天空、巡游世界。
但最想要的,还是女人。前女友是他家乡职业学校的同学。到了婚龄,阿青仍不能为她买车买房、甚至不能为她张罗一场像样婚礼,她便离开了阿青,像当初看见他弹吉他而爱上他时一样突然与坚决。
阿青背上吉他来到大理,任头发疯长及肩、不修边幅,一件廉价的黑色T恤,套上宽松的牛仔裤和黑色的人字拖。阿青在酒吧唱自己写的摇滚,面对姑娘时冷酷木讷,不喜所谓「撩妹」。他认为那些谈话大多无聊,浪费时间。但大理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无论它怎么流逝,也没有使阿青的创作有实质的提高。
今晚唱得不开心,他喝了很多酒,现在还有些醉意。阿青眼前,又浮现出女人薄裙里的肥大屁股。
睡下总觉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十多分钟后,他一把抓过衣裤套上,拿起手机、趿拉着拖鞋冲出门,往下午那个巷子快步走去。路过小卖部时买了瓶二锅头,他大口大口地喝酒,想让自己放松,修摩托的混混告诉过他:放得开,才玩得High。
阿青去巷子里找那些女人,带回自己在天台的阁楼。他虽然还是学不会在酒吧浅吟低唱: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姑娘啊,你来不来?」
学不会以「故事和酒」引来漂亮的姑娘和她们谈论「阿弥陀佛,么么哒」、「好吗,好的」,但面对巷子里那些坦白交易的女人时,他已不再局促了。
强迫自己进入状态,匆匆了事。
天空下起雨来。阿青感到一阵阵疲惫和厌倦,这种疲惫和厌倦的感觉真实让人憎恶。阿青想了一遍又一遍:
「使一切变得平庸、在漫长的日子里击倒自己的,究竟是什么?」
一件素色套头衫加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再套上一双「飞跃」小白鞋,梳一个简单的马尾,叼一支烟,瘦高的姑娘秦紫看起来清新自然,谈话间又显出几分泼辣与干练。
三年前从一所美术学院毕业,她南下深圳,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上班。每天早起去赶「肉罐车」似的地铁,晚上睡倒在电脑前面。周末,秦紫会涂上黑色的眼影和唇膏,戴上大大的圆耳坠、穿上透视的黑色短裙和绑带高跟,喷上「地中海花园」,去夜店蹦迪。
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闪烁暧昧的灯光里跳舞,等待猎物的出现——尽管在别的男人眼里,她才是可人的猎物。
蹦到后半夜,秦紫从不带男人回自己的住处。要么去酒店开房、要么去男人家里。完事便自己打车回去。她不想和那些男人多聊,更不愿和他们度过余下的夜晚。
她感到厌倦:无论是睡在家里的电脑前,还是睡在陌生的床上,都只是在透支自己。她夜夜失眠,烟瘾越来越大。
「闲散和吻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味道才是最甜的。」
秦紫想舒缓自己,辞去工作去一个地方,任由自己读书画画、逗猫饮茶。
她想找回闲散,特别是找回吻。和陌生男人做,她从不接吻。
就这样,秦紫来到洱海边,长住进了容宴蓝和perez开的客栈。
她带了两本喜欢的书,背上很久没用过的画夹,整日在大理闲逛。有时去洱海旁写生,但心中总空空落落,不时仍焦躁不安。「过来人」告诉她:你需要在这里多泡上一段,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一天,她在古建筑的广场画画时遇到了也在那写生的张桦。天快黑时,留着大胡子、梳着发髻,穿着亚麻盘扣衣的张桦邀请她一起晚餐。起初,她对这个中年男人并无特别的好感,但一人总显得落寞,况且,张桦很懂得逗她开心,跟她讲了许多有趣的「江湖故事」。
一连好几天,张桦都去客栈找她,一起吃饭聊天,四处写生。他还邀请秦紫去他租的院子,一起买菜做饭。他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亲切感,她隐隐地感动着:记得小时候爸妈感情不合,她每天提心吊胆。她很少看到妈妈笑,矮小多病的妈妈一吵架就会跟她哭诉,告诉自己爸爸是个多么冰冷而自私的男人。小时候很想见到爸爸,如果哪天父母在家里一起做一顿饭,她会高兴到天上去。现在,和张桦逛着简陋的菜场,在他的小院里忙前忙后地做菜,埋藏在心底期盼已久的温馨画面出现了。
秦紫知道了张桦靠画画为生,来大理采风,准备办一个画展。她对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当他略为尴尬地接听电话时,秦紫猜到他是有妇之夫,但她也不问,反而懂事地自己走开。
在深圳时,秦紫的心是封闭的,夜店里遇到的男人不会再见第二次。她和男人聊天,更不会对某个男人产生什么情感的牵连。有时她甚至觉得夜店是一个很傻的地方:如果把音乐和灯光一关,男男女女在舞池扭动身躯、如痴如醉,谁也不认识谁,是多么一幅可笑的场景。
而来到大理,她希望把心打开一些。来这里的人都没有什么目的,或者说都带着某种目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对张桦有了某种依赖感,她不知道是否自己卸下了在城市的伪装,心开始柔软了些——她知道心中始终有个女孩儿,希望得到温暖和关爱。
这种依赖在张桦离开大理短暂回家的几天中变得异常强烈起来。突然自己又变回了一个人,在大理孤零零地哪也不想去,甚至不想去画画、不想看书、不想吃饭。躺在床上想张桦,知道他正和老婆在一起,心中有些醋意,但强忍住不联系他。久违的不安和对冷漠的恐惧又袭上心头。秦紫觉得很煎熬。这样的心境,无论如何不是当初来大理时会想到的。容宴蓝察觉到她整天窝在客栈抽烟、神情衰弱又很少吃饭,便和perez做了好几个菜,叫上秦紫和阿青,一起在天台吃晚饭。
吃饭时,容宴蓝问醉醺醺的秦紫「之前那个画家呢,怎么没见过来了?」秦紫苦笑着跟大家说自己的故事,说到一半掐灭了烟头问:
「我他妈是怎么了?」
perez笑嘻嘻地说:
「忽冷忽热,这他妈是个老手。」
容宴蓝狠狠瞪了他一眼。阿青哈哈地笑,拿起吉他弹起来,戏谑地给秦紫唱辛晓琪的「味道」: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秦紫举起手中的酒杯喊:
「阿青,你他妈闭嘴!」
无可奈何地度过了四夜五天,张桦在微信上告诉秦紫他回来了。秦紫慌忙下床,穿着拖鞋跑到客栈外租了一辆电动车,不顾天黑路远赶去张桦的住处。她紧紧抱住张桦,一边吻他,一边扒下了自己和他的衣服…
之后他们一起背上画夹环游洱海,钓鱼、野泳,遇到好风景就停下画画。晚上秦紫拥着张桦的身体,睡得很安稳。她不去想自己有多爱这个男人,只想枕在他胸口,沉沉睡去。
一个多月后,面容憔悴的秦紫坐在床上对着验孕试纸发呆。张桦回家后再也没联系过她。终于拿起电话打给他,告诉他自己怀孕了。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说了一声「嗯」。秦紫拿下嘴里的烟头,狠狠往自己手臂摁去。
挂了电话,她是不可能再找他的,连手术钱也不会让他出一分。
打车从医院回住处,秦紫提前下了车,在路上慢慢走着,腹内传来阵阵疼痛。她索性坐在路边冰冷的石椅上,点一支烟,看着那些往日不曾留意过的街景:太阳正在落山,白天的余热散去,众多酒吧陆续开门了,酒保们忙碌地在街边揽客,一群群男男女女,走进一间间拥挤的屋子。
秦紫心想:其实这座古城和别处没什么不同,她感到一丝嘲弄和无奈,把烟熄灭,忍着腹痛起身离开。
容宴蓝和perez常常听见秦紫躲在房里哭泣。夜晚,这种哭泣的声音让他们难以入眠。阿青带回来一个个他曾说绝对不会靠近的女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北京,容宴蓝会不以为然,但发生在她喜欢的大理,在她梦中的小院里,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不堪…
某天,「一定要保护好洱海」的标语贴满了大理的大街小巷。禁令下达「洱海周围的所有旅店餐馆必须接受排污检查,净化系统建立起来之前一律不准营业」。容宴蓝面对不能做生意的尴尬,却莫名地轻松起来。她甚至怀念起在北京上班的日子:工作虽乏味,却单纯,自己也简单,该工作时就工作,只要有空就拉闺蜜逛街,看电影、吃甜品…也挺好。
人总是这样,过了岔路,就总觉得另一个入口更好。
一天,容宴蓝找到又在天台抽烟喝酒的perez商量:
「不如把客栈转让了吧,回北京。」
perez沉吟片刻说:
「好。」
费尽心力搞起来的客栈,转让却出奇顺利,不久便有一对来自杭州的同性恋朋友接手。他们相爱多年,但都各自「形婚」。同样受够了在大城市的压力和分离,他们想来大理借开客栈为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容宴蓝抱着女儿,perez拉着行李箱,站在客栈门前回望这栋小楼,眼神里只有疲惫,没有惋惜。
「云的南方」永远还有南方。「生活在别处」就像拙劣的巫术。全情投入的人们筋疲力竭后,没有一个,能驱走往日心魔,过上幻想中「真正想要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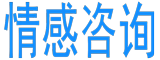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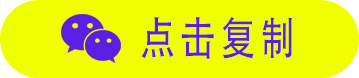




评论列表
有情感误区能找情感机构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心情也好多了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被拉黑了,还有希望么?
被拉黑了,还有希望么?